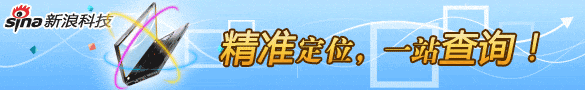蓝色的舌头(3)
我两点四十就到了那家包子铺门口,可是左等右等,等到将近四点,也不见有类似苏迎描绘的人物。就算他不认识我吧,我在人行道上呆立了这么久,不断地看表,他也该知道我就是他约的人了。
一直等到将近五点,我才怀着沉重的心情,上车回家。我原是想为社会尽一点义务的,说来惭愧:我这时已经泄了气,完全放弃了原来的打算。如果他此时来还我小儿子的舌头,我会毫不犹豫地把五千块钱交给他。
在我下了汽车,拐进笔杆胡同的时候,我忽然听到背后有急促的脚步声。我本能地站住,回过头去,看见一个身材很高的家伙匆匆走来。
“姓苏的,”他停下脚步,前后看看,“带来了么?”
“什么‘带来了’?”我反问他。
“装他妈什么傻!”他说,“五千块呗!”
我打量他一下,觉得苏迎对他的描绘还是准确的。只是他比我想象得年轻些,而且脸上多了一副“蛤蟆镜”。
我把手伸进衣袋,他警惕地往后一跳,动作十分敏捷。看见我掏出的是一叠百元钞票,他呲牙一乐,走上来接过,飞快地点了一遍。
“行!够朋友!”
他把钞票往上衣袋里随便一塞,又随手掏出个纸包来,递给我。我打开检查了一下,也收起来。
“那个蓝的就送给你儿子当玩意儿吧!”
他慷慨地说。我冷笑了一声:
“谢谢你!”
他皱了皱眉头:“少他妈来这套酸溜溜的!”接着,又冒出一句非常下流的话。
我挑战地说:“不用说,你嘴里也安着个蓝舌头!我倒想知道,那脏东西是哪儿弄来的?”
他满不在乎,嘻皮笑脸地说:“就戳在这儿聊?不够意思吧!我看你是个朋友,走,喝一杯去,我请客!”
我不知道他真想告诉我点儿什么,还是认为人多的地方比这儿更容易溜悼。或许,酒馆里有他的同伙接应。不论怎么样,我不能就这么放他走。我点点头:
“好吧!”
我们到了大街上,走进一家很像样的饭馆,找个僻静的角落坐下。我把菜单递给他让他点菜。他头一歪,问我:
“什么意思?”
我说:“小意思,我请你。”
他说:“讲好了我请你的嘛,你看这事儿闹的!”
我说:“随便点几个吧!”
他说:“那我就不客气啦!”也不看菜单,一口气向来开票儿的服务员说出七八个菜名。我又去给他买来一瓶白酒。他接过瓶子,用于指头“当当”地弹两下,吹了声口哨说:
“好酒!”
喝了几杯,他的脸泛了红,话多起来,“蛤蟆镜”也摘了,桂在上衣的口袋上。
“你的那个娃子,满招人爱的!”他热情地夸奖着,虽然带着一大串脏字,毕竟是句好话。我说:
“谢谢你!”
“又他妈犯酸!”他皱着眉头评论了一句,接着说:“我跟在他后头走了两趟,知道你们家住哪儿。我也偷看了你几天,知道你是个好人。你昨儿个一接着我的信就上储蓄所取钱,刚才才又傻里巴唧地站在马路崖子上看了两个多钟头的表,哈哈哈哈……”他一边笑,一边端起小酒杯,一仰脖儿,把酒喝光。
我真想照准鼻子,狠狠给他一拳。可我只是伸手拿起酒瓶,把他的杯子斟满。他乜斜着眼看着我:
“怎么,想把哥们儿灌醉,好送到派出所去?”
我没办法,只好把自己的杯子也倒满,跟他一对一地喝。
等到他说话舌头发短,我也觉得天旋地转了。
他的话却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下流。他伸出蓝舌头叫我看,比比划划地说:
“这又怎么啦?非得说话冒酸气才算好?瞧把你们两口子急的!准知道要八千块你也得给!有的爹娘,见自己孩子换上蓝的,还高兴哪!碰上那样的主儿,我就算白费蜡,甭说五千,五块他也不给呀!”
我问他:“你那蓝舌头儿,哪儿弄来的?”
他哈哈大笑说:“怎么着,也想弄俩零花钱?还要到哪儿去弄啊?你瞧着!”
他伸出舌头,一把揪下来,往餐桌上一丢,又一伸,嘴里又出来一个舌头,他又一揪,一丢……就这么吐出一个,揪下一个,跟个魔术师似的,没完没了地表演起来。不大工夫,餐桌上、菜盘子里丢满了蓝色的舌头,总有七八十个!
“瞧见没有?”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用胳膊在桌面上划一个大圆圈,“一个五千元,这得值多少钱!钱还在其次,大爷我爱听这个曲儿!我一听‘谢谢’,‘对不起’那些冒酸气的话就恶心,听这些小宝宝说话,多开心!它们叫起来,就跟小鸟儿唱歌似的,那个美呀……不信?你听着!”
他猛地向桌面上击了一拳,“砰”地响了一声之后,桌面上那许多蓝舌头突然一齐蠕动起来,活象一堆大蚂蝗。它们一边蠕动,一边各自发出吱吱哇哇的声音来。有几个大喊“哥儿俩好啊——八匹马!七个巧!”另外一些就捉住对儿厮骂,骂得要多难听有多难听。我觉得全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
他得意洋洋地说:“怎么样,比四个喇叭的录音机还好听吧?哈哈,我要给所有的孩子都换上它,让他们跟一群会唱歌的小鸟儿似的!你是零卖,还是批发?价钱好说!”
他从衣袋里掏出个大塑料袋,把满桌子的蓝舌头,连同那些沾满剩菜残羹变得湿漉漉的,统统装了进去。
走出饭馆,天已经黑了。那家伙向我一挥胳膊说:
“行啦哥们儿,后会有期!”
我冷笑一声,跨上一步拦住他:
“你想就这么走?”
那家伙变了脸色,像弹簧一样,“腾”地跳开,抽出一把雪亮的刀子。我一个箭步窜到他面前,把他胳膊往后一拧,同时把他的手腕朝上一掰。他“噗嗵”一下跪到地上,刀子也‘当啷’一声掉在人行道上。
就在这时,我觉得身后人影一闪。我还没来得及转身,就觉得脑袋“嗡”了一声,什么都不知道了。
等我醒来时,我看见周围亮得刺眼。天花板是雪白的,墙壁是雪白的,我身上的被子也是雪白的。我们家的被面是花的,这不是我们家的被子!
我是躺在医院里。
一个熟悉的面孔靠近我,这是她——我的意思是说,这是苏迎的妈妈。她的眼睛里有泪水,可是脸上满是快乐,多么怪!
接着,我又看见苏迎。他走过来,抓住我的一只手。他说:
“爸爸,您怎么睡了两天也不醒啊?我和妈妈都急死啦!现在您醒了,我可真高兴!”
他的妈妈低声告诫他:
“先别和爸爸说话!”
可是我爱听他说话。他说了这么一大串,连一个脏字儿都没有,我比他还高兴呢!我问:
“妈妈已经把你自己的舌头换上了吧?”
我把苏迎问得呆住了。我再看他的妈妈,他妈妈也敛起笑容,满脸忧虑的神色,眼泪都快流下来了。
他们是怎么啦?
大夫走过来,命令我不要说话,我觉得有些累,就闭上眼睛,不想一闭上眼睛就睡着了。
低低的谈话声把我弄醒了。我睁开眼睛,看见一个梳着短发的姑娘,正把一网兜水果放在我床头的白漆小柜子上。我认识她!
“李老师!”我有点儿难为情地叫了一声,“真对不起,我到现在也没去给您道歉……”
那姑娘怔了一下,接着脸红了,向我点点头说:
“您为我受苦了……我们还不认识,我姓王,叫王××。”
天哪,李老师姓王!
当天晚上,我同室的病友递给我一份晚报,指给我一个标题看。那标题里有我的名字。
我把这篇报导看了。
报导说,我在下班的路上看见饭馆里走出两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他们拦住过路的某厂青年女工王××,向她说些“污言秽语”。我上前劝阻,“二人不听,反而破口大骂”,我“据理相争”,对方一人就掏出匕首,朝我刺来。在我“奋起自卫”时,另一人操起一块砖,“猛击”我的头部,将我“打昏在地”……
莫名其妙!我对病友说: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那是为了蓝舌头!我想抓住一个诈骗犯……”
我的病友咬住下唇,好像在那儿拼命忍住笑,我实在不乐意看他那副怪样子!一个是忍住泪,一个是忍住笑,谁都不想听听我的意见,没办法,我只好揪住来查病房的大夫。
谁都没有这位大夫好。只有他不说我“神智不清”,只有他相信我的话。他耐心地听我讲蓝舌头的前因后果,还边听边点头说:
“噢,原来是这样!”“噢,是这样的!”
都听完了,他说:
“我看你说得很对,一定不能让我们的孩子换上蓝舌头!可是,你现在要好好休息,别的事情由我们来办。你放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声明:新浪网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