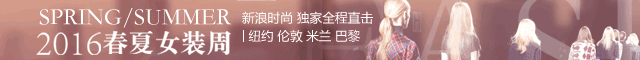嗞~~,鲜嫩烤肉上的油花在铁盘上欢快地跳着舞。
刚刚在医院敲定了剖腹产手术日期的我一边大快朵颐,一边盘算着仅剩的几天里还有哪些美味一定要赶在手术前享用一遍,才能死心塌地地乖乖进产房。
是的,没错的,怀孕时的那些忌口,比起坐月子来,简直不值一提。如果你想母乳喂养的话,那么恭喜你,有些美味可能一两年内都与你无缘了。
想当初怀孕怀得突然,既没有备孕,也没有知识储备,医生随口说个指标都紧张得不得了。最夸张的时候,只不过因为孕酮比前一次测的低了一点点,就每三天跑去医院抽一次血。孩子爸爸一边心疼我扎得都是眼儿的手,一边每隔三天就低眉顺眼地哼唧让我再去医院验一次血。现在想来,真是好笑,但当时真是全副心肠都挂在这个未成形的小细胞团儿上了。
由于刚怀孕需要建档时单位离协和比较近,所以最初的检查都是在协和国际部。可能是赶上马年,马宝宝比较受欢迎的缘故,即使国际部也人满为患。至今我仍深深地记得自己抱着一丝希望打电话给协和国际部咨询的时候,护士直截了当地说没床位不能给建档,后面一句则更让人惊讶且无奈:能排上床位的现在还没怀上呢!
既然不能建档,且几次去检查人都实在太多,加上宝爸那时工作甚忙,无法保证每次都陪我一起去检查,剩我一个人忐忑地挤在护士台前一群人高马大的宝爸们中间的经历实在不美好,我们最后选择了将台路的和睦家医院。
其实在决定选择私立医院之后,很大一部分的因素就是靠眼缘了。当初选择和睦家,一是因为它有血库,万一遇到紧急情况可以应急;二就是去参观的时候,陪同人员都让人感觉很舒服且专业,产房也都宽敞明亮。
虽然在孕期各种调整胎位的姿势每晚都做,但豚宝仍坚持淡定地坐在肚子里。其实宝宝一直都很淡定,不淡定的是我们这一对刚刚晋级的父母而已。因为一直希望顺产,所以坚持等豚宝转头一直等到8月7号产检,而预产期就在8月13号。淡定的医生这时也不淡定了,逼着我一定要尽快安排手术,否则如果提前破水,来不及赶到医院会容易有各种风险。而当时的我,因为抱着壮士断腕的决心,准备吃饱喝足生娃娃之后做个每天均衡饮食的好奶牛,所以在医院就差上演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戏码,一天一天地跟医生磨,硬要把手术日期定在了8月10号。
从医院出来,就是文章最开始的那一幕。吃得开心的我,并不知道自己的小算盘全落了空。豚宝既不肯听我的转成头位,当然也不肯听我的等到两天之后再出来。
吃完烤肉回到家,我心满意足地躺在床上,想着这两天排队等着我的好吃的,抱着孕妇枕睡得正香,突然!
噗!我瞬间惊醒!赶紧推旁边睡得呼噜呼噜的人!快起来!破水了!
旁边的人眼睛完全睁不开,反问我:你怎么知道是破水了?你是不是尿了?
气死人了!
虽然说我以前也怀疑过,随着孕期靠后,些微的尿失禁也属于正常,妈妈们怎么就知道自己是破水了呢?可是事到临头,这种感觉真的不一样好吗!即使是在睡眠中,也能清晰地感觉到好像是一个吹满气的气球突然破了一样,羊水哗地一下流出来,是绝对不会弄错的!
就这样,我自我感觉非常镇定地指挥旁边的人给医院打电话,给父母打电话,以及拿前几个礼拜就开始陆续装好的待产包。可是,旁边的人一边迷迷糊糊地拿着我的手机,疑惑到底是拨打和睦家妇产还是和睦家预约,一边继续坚持不懈地问:你是不是尿了?你其实是尿了吧?
气死人了!气死人了!
迅速地让孩子爸爸拿来了隔尿垫,他揉了揉眼睛,终于承认是破水了:虽然没有颜色,但是觉得你应该尿不了这么多吧?
实在是生不起来气了。
终于被认可是破水之后,便顺理成章地叫醒父母,收拾东西,按医院的指示尽量平躺,不要动,叫救护车。这个时候叫救护车应该还是更为理想的选择,一般的家用车和出租车可能会受到交通的影响,而且也没有一些应急的设施,比如救护车的担架就可以让你保持平躺的姿势从家里的床上运到医院的床上。
从凌晨一点多破水到两点多躺在病房的床上,我的心里踏实了。我开始感觉自己的宫缩,都说宫缩的感觉跟来大姨妈差不多,还真是的,只不过强度大了不少。虽然觉得剖腹产是难免的了,但是躺在产床上的我还是不死心,让医生做了一次B超,希望豚宝能转成头位。结果豚宝很有主意,仍然淡定地坐在肚子里。只能等着手术啦!等手术的时候,可能是因为知道要剖腹产的缘故,我一点儿罪都不想受了,有一点宫缩都觉得疼得不行,生怕豚宝等不到手术自己发动。幸亏医生来看完监测数据,说了句你这只有一次像点样儿的宫缩,早着呢!
四点多,我终于从病房被拉到了产房,据护士说,她们这一晚上已经做了8台手术了。碰巧当晚值班的医生正是我当初预约的医生,我正在边套近乎边忐忑的时候,一直给我做检查的常玲大夫来了,我顿时就像有了主心骨。不得不说,虽然剖腹产已经不算什么了不起的手术,但是有个从孕期就了解你情况的医生真的让人踏实很多。护士向我和宝爸一一介绍了医生和麻醉师,就开始做手术的准备工作,我跟宝爸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儿。常玲大夫看着护士准备的工具,突然开玩笑说,你们干嘛把好东西都藏着,就给准备这种线?护士一下就茫然了,常大夫笑了,说看我来找!躺在床上的我听着一通乒乒乓乓,然后是常大夫炫耀的声音和护士的玩笑:也就是您,我们哪知道有这好东西啊!常大夫紧接着站到我的旁边,跟我说,我给你用的可是缝脸用的线呢!她们一般都不知道!
虽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是经过这一下,我的忐忑的心竟然一下平静了,只剩下对医生全然的信赖和期待。按照麻醉师的指导,我拱起腰,上麻醉,等麻醉生效。上麻醉会疼一下,但绝非不能忍耐,而且很快就过去了。
躺在那里的我其实除了冷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感觉,只听见常医生开心地说了句:是个坐宫娘娘!我和宝爸瞬间惊呆:是个女孩儿啊!宝爸貌似还追问了句啥,常医生又肯定了是个女孩儿,我们才开始傻乐。从怀孕以来各种被人说是个男孩儿,让喜欢女宝的我俩纠结得一度放弃了希望!所以说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逆袭了呢!哈哈!
护士抱过一个白白的娃娃来让我亲,大概看我很是清醒,并没有问我是男孩还是女孩。白白嫩嫩的皮肤,闭着的长长的眼睛,红艳艳的小嘴,此生无论她长到多大,在我眼里应会一直是这样柔嫩的面孔。
听人说,女人生完孩子会分泌一种神奇的激素,使她忘记生产的痛。诚然,孕期的辛苦,生产的忐忑,术后刀口恢复的疼,至今仍历历在目。但是,现在看着那当初白白的小脸一点点变圆,当初闭着的小眼睛带着笑凝望,当初红艳艳的小嘴不停地喊着妈妈妈妈,我相信那种神奇的激素真的存在。
只为了那一场最美的相遇。
张笑楠
——本文摘自由漓江出版社北京中心授权的《只有妈妈知道》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