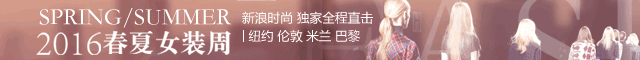王子莫今年六岁了
王子莫今年六岁了准确地说,她今年,应该六岁了。由于没有了出生证明跟任何身份信息,带养她的保姆古新菊,只能估算她的年龄。
王子莫可能是东北人。事实上,这也是古新菊自己琢磨出来的。古新菊听过王子莫生母的东北口音,由此她自己判断出来的。
三年前,在深圳,四十出头的广东五华人古新菊,被王子莫的妈妈桂花雇佣成为家里保姆。此后,桂花消失不见,古新菊说,她独自抚养王子莫长大,再没收到来自孩子家人给的半分钱。
1000个日夜:
陌生人成亲人
春去秋来。三年就是1000多个日夜。如果古新菊每晚哄子莫入睡,都要讲一个故事,估计都能出书了吧。
已过立秋,接连几天的阵雨过后,八月的深圳,天空澄澈,阳光也变得温柔起来。
古新菊推着一辆老式的自行车,在人行道上缓缓走着。子莫穿着粉红色小裙子,乖乖地坐在车后座,双腿不时摇摇晃晃,嘴里咿咿呀呀地自言自语。午后的阳光慵懒而和煦,路旁的树木郁郁葱葱,清新的气息扑鼻而来,古新菊却无暇顾及这好天气。
九月份就快到了,孩子上学怎么办呢?为了这件事,她已经愁了几个月。
“大姑!”子莫脆生生地一喊,古新菊才回过神来,加快了脚步。四点半之前她要赶到当地税务局的饭堂炒菜煮饭。这是她今年找的一份工作,在食堂负责员工的一日三餐,一个月能挣3000多元。在深圳,这工资并不高,然而,对古新菊来说,这笔钱很重要。
新菊和子莫,居住在龙华新区观澜辖区长湖头村内,这里距离观澜人民医院不到300米,交通倒是便利,只不过她们几乎都不走出村口。食堂的工作是她唯一的工作,原本还能兼职做做保姆,但自从带着子莫后,她的时间被挤压得只能边工作边带娃。
子莫很活泼好动,每每古新菊在饭堂干活,她就一个人到处疯跑。问及妈妈在哪里,子莫一脸懵懂:“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来接我。”
妈妈桂花离开的那年,是2013年。那年7月,没有多少文化的古新菊,决定找份保姆的工作养家。经龙华的一家保姆公司介绍,她在龙华弓村找到了一份工作,到一位名叫桂花的女人家里当保姆。子莫的妈妈桂花和她协议,以每月3000元的价格负责带子莫,包吃包住,这份待遇对古新菊来说,还是相当不错的。
在古新菊印象里,桂花人长得挺漂亮,女儿子莫也活泼可爱,喜欢黏着她,奶声奶气地叫“大姑”。那时候的她,已经是4个孩子的妈。每天,古新菊坐公交车来到弓村,爬上十楼,到桂花家中带子莫。除了带小孩,她还要买菜做饭,工作虽然单一,但每天也是忙忙碌碌。
或许是因为看古新菊辛苦,又或许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桂花决定每个月多付她1500元,总共4500元的价钱,条件是,古新菊得把孩子接回家里带。
新菊没多想,就答应了。
无法立案的案情:
有娘等于没娘
古新菊跟丈夫育有三儿一女,大儿子24岁、二儿子23岁、小儿子21岁,最小的小女儿今年也19岁了,为了生活,4个孩子都出来找工作了,丈夫不在深圳,在老家广东五华做点农事帮补家里。平日里一家人挤住在一间小出租屋里,但是,大家对子莫都十分疼爱。
然而,带孩子这份工作进展得却并不顺利。
起初,桂花还按月付新菊工钱,但给着给着,就断了。新菊并不担心,在她的简单逻辑里,孩子都在自己手里,怎么可能不给钱呢。没多久,桂花因为交不起房租,从弓村的出租屋里搬了出来。古新菊心眼实在,看桂花实在交不上房租,就暂时收留了她。“后来,她住哪里就不知道了,有段时间来长湖头村这边跟我们一块住。”在新菊印象中,桂花是名足浴师,也时不时的不回来,她心中有嘀咕,但她不说。渐渐地,桂花来看子莫的次数越来越少。
2013年年底,那个冬天冷得出奇,深圳最低气温多次跌至10℃以下,并伴随着潮湿天气。一天,桂花对新菊说,身上没有什么钱了,要去海南找孩子的爸爸要点钱。这是桂花和新菊的最后一次见面。
2014年1月6日,古新菊到辖区内的龙城派出所三联警务室报案登记,警方也试着查找了小孩的亲生母亲,但最终无果。不是拐卖,不是丢弃,不时地还有单向联系,仅凭这样的情况,根本达不到警方的立案标准,况且从那以后,古新菊就没再来报案了。
有人建议古新菊,把孩子直接抱去市福利中心门口,别说其他情况,“后续就好办了”。但古新菊听了半天,愣是没想明白,“孩子怎么能说扔就扔呢?”
2013年至今,桂花曾主动联系过古新菊,但她的电话号码总是不停地换着。“妈妈快点带钱回来,我想你,我想回去。”每次接到妈妈的电话,子莫带着哭腔的声音,总会刺痛古新菊的心。尽管“大姑”对她很好,尽管4个哥哥姐姐也疼她,但在子莫幼小的心灵里,却始终有一个“妈妈不要她了”的阴影。3年来,古新菊不断尝试联系桂花,但每次电话都在接通后,又被快速挂断。
今年7月份,桂花打来最后一通电话,号码显示为云南丽江。桂花说,她在中缅边界做着生意,并告诉子莫:“妈妈坐火车要两天呢,两天后就回来找你。”,但这“两天”,又让古新菊白等了一个多月。
听说妈妈即将回来的消息,子莫一度又满心欢喜。但对于妈妈数不清的又一次失约,子莫的心里有多少失落,古新菊就有多少无奈。
有学问的表哥:
义务跑腿奔波
“我觉得她妈妈肯定是有什么事,有事在身的人,说话就是不停地变。”说这话的,是新菊的表哥申旭东。他跟表妹古新菊,此前已经有好十几年没见过面了,如果不是因为早年在河源做过老师,是古新菊眼里有学问的人,他和表妹的重聚还不会这么快。
古新菊找到表哥申旭东,希望他能帮自己讨回公道。最初,古新菊希望,桂花能把所欠的工钱都还上,慢慢地,钱开始变得“不那么重要”,子莫3岁了,古新菊开始着急孩子上学的事,表哥为了帮她,跑遍了大大小小的职能部门:龙华新区信访办、民政部门、龙城派出所……最终无果。龙城派出所答应有消息就通知他们,街道办让他等电话,民政局说这事不归他们管,求助法律部门,工作人员回复称:“她妈妈不回来,就算官司赢了也没用。”
孩子渐渐长大,眼瞅着邻家的孩子都要高高兴兴上学去了,子莫只能抱着准备去饭堂上班的古菊,一口一个“大姑”地喊着。
求助媒体似乎是古新菊最后的希望。她眼巴巴看着记者:“能帮孩子上学么?” 如今在她眼里,什么问题都比不上子莫上学的问题重要。
说完这句话,古新菊又得开始忙活了。食堂里,她洗菜切菜,子莫在一旁蹦蹦跳跳。古新菊把等着上锅的材料切好备好,擦了擦湿漉漉的手,坐下来喘了口气,额头上还带着汗珠。子莫则拉着“大姑”的手嘻嘻地笑,朝古新菊的脸颊重重地亲了一口。她或许还不知道,上学的路,还有多少困难在等着他们。
孩子收养:
“万一哪天他妈回来找了呢?”
在表哥申旭东的眼中,古新菊虽然“包容、有爱心、善良”,但有点傻:“揽着个别人家的孩子,还天天操心她啥时候能读上书……”
为了帮表妹,申旭东甚至还开始研读起政策性文件——“在深圳读书需要什么证件”、“1+5文件是什么”……
申旭东了解到,在深圳,适龄儿童要读书,就得过“1+5”文件的关。“1”指的是《深圳市关于加强和完善人口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文件;“5”指的是非深圳户口在深圳读书需要提供“5证”:一是适龄儿童转学学生的出生证、父母原籍户口本、深圳居住证或暂住证;二是房产证明,无房产者由打工者所在街道办房屋租赁管理所提供租房合同登记、备案材料等;三是就业和社保证明,或者本市工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等证明;四是打工者现居住地街道办事处计划生育工作机构出具的计划生育证明材料;五是原户籍地乡(镇)以上教育管理部门出具的就学联系函,或学校开具的转学证明。
但新菊和子莫,拿不出半张材料:爹妈没在身边,联系不上;子莫在哪家医院出生,古新菊不知道;子莫是不是黑户,也得亲生母亲来证明,万一她有户口呢?甚至有人怀疑过,孩子是不是古新菊自己偷生的,这让年近五旬、生性憨直的她也觉得哭笑不得。
这座大山绕不过,那还有没有什么别的途径呢?深圳市福利中心相关工作人员告诉晶报记者,“原则上福利中心只能负责接收由警方认定为弃婴的孩子,一旦被收养,福利中心可以作为监护人为孩子办理相关证明文件,继而办理读书上学,但他们没有权利就这样把子莫接收了。”
“万一哪天孩子他妈回来找了呢?”
工作人员给出的建议是:还是先报警。如果王子莫的父母一直不来认亲,孩子连黑户的身份都难以认定,不管在哪读书都成问题。
而让古新菊更尴尬的是:龙华警方查证的资料显示上,古新菊报案时,王子莫当时登记的年龄仅为2岁,若据此推算,子莫今年只有5岁,够不够得上上学适龄儿童的身份,还是两说。
“带着小孩难上班”、“小孩几个月连着大病两场,发烧到40℃,打了几天吊针,看得我都怕”……新菊生活的窘迫,以及对子莫的疼爱,申旭东都看在眼里。也正因如此,他为表妹3年来的付出而愤愤不平,逢人就痛斥桂花的无情:“连自己的孩子都不管不顾,她(桂花)怎么狠得下心!”
古新菊提起桂花,更多的却是无奈。“她妈妈不要,我要!”“她要想带回去”,新菊顿了顿,“也不是不可以,但我养了3年,(桂花)一定要给补偿。”
“想妈妈么?”
每当有人问及这个略显敏感的问题,子莫就会不假思索地点头,然后补充说:“我妈妈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她想回到亲生妈妈身边是真的,但念着“大姑”1000个日夜的好,也是真的。
“如果有一天,妈妈来带你走,会舍不得大姑么?”
“等我长大了,再回来找她。”子莫指了指仍在厨房里忙碌的古新菊,笑颜如花。
来源: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