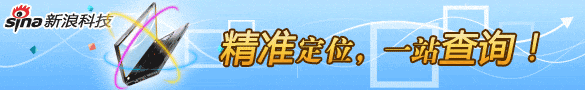《爷爷铁床下的密室》选摘(3)
二 意外发现
钢琴女孩儿的琴声让我想入非非,我幻想着变成一只凶猛的鹰,终日守护着弹琴女孩儿。因此,巫女保姆说我是个复杂少年。
我有一个日记本,里面记的都是我的秘密。把心事记在日记里,往往是女孩子们津津乐道的事情,而我也喜欢这样做,所以我时时感到不安。
在日记里,我喜欢跟一个女孩儿对话。
这个女孩儿就是小白。她比我高一个年级,在一所私立钢琴学校上学。她长得瘦瘦细细,喜欢穿乳白色衣裙,走起路来飘飘如仙。她的钢琴弹得很好听。很久以来,这个女孩儿一直占据着我心里的世界,挥之不去。我希望她能转到我们学校,这样,我可以有更多的机会看见她。我还梦想着她是我的姐姐,我们说说笑笑一起上学下学。这是我的秘密,谁也不知道。
像别的女孩子那样,我的日记本锁在小箱子里,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才把它拿出来,悄悄与钢琴女孩儿对话。父亲母亲离婚后的许多日子里,我之所以没有一点儿浮躁和消沉,很大程度上与日记里的钢琴女孩儿有关。
小白家住的是一幢旧式木结构小楼,家里有一位会弹钢琴也会修理钢琴的保姆。小白每天早晨要练习一个小时的琴,放学回来还要练习一个小时,如果她不用心练的话,保姆就会惩罚她,让她再练上一个小时。小白对我说,她很怕看到保姆发脾气时的眼睛,那眼睛让她想起住在深山里的巫女。
我喜欢听小白弹钢琴,一听到她的钢琴声,心里就禁不住产生许多奇妙的幻想,幻想着我变成一只凶猛的鹰,绕着小白家的楼顶久久盘旋;钢琴女孩儿是一只小巧雪白的鸽子,在鹰的保护下,她安详地停在楼顶上瓦垄间梳理着羽毛。有时候,我又幻想着自己是一只猫头鹰,威风凛凛地守护在小白家的客厅里,小白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我的视线,小白家的巫女保姆在有着尖喙锐爪的猫头鹰面前,变得惶惶不可终日。
从前,我经常找点借口跑进木楼,看小白练琴。有时候女孩儿已经结束了练琴,而我仍痴痴地站在钢琴旁。
小白说:“我都不弹琴了,你怎么还站在那儿啊?”
我说:“我耳边还有钢琴声呢。”
小白说:“是你的幻觉吧。”
我尴尬地用手指挖挖耳孔。
小白笑了:“你真好玩。”她把我拉到她的桌边,拿出好多画报给我看,我安安静静一直看到窗玻璃罩上一抹暮色。
后来,我的父亲母亲离婚了,再去小白家,那个描着两条黑眉毛的保姆,便找出种种借口将我拒之门外。
我恨这个巫女保姆,在薄荷巷子里的墙上画过丑化她的漫画。可每当听到小白的钢琴声,我的血管里便涌起一股冲动,两条腿坚定不移地向小木楼走去,躲在楼下悄悄地听。我希望巫女保姆惩罚小白,让小白多弹一会儿钢琴,让琴声给予我更多的奇思妙想。
我心里一直后悔那天没有上前扶起受伤的小白,她和自行车一块儿摔倒,摔得那么重,而我却逃掉了。我担心小白家的保姆会把这件事与我联系在一起,因为她认为我是一个复杂少年,她拒绝我和钢琴女孩儿来往,就包含这层意思。
那几天我很愧疚,害怕见到小白,但是每天上下学经过小白家门前时,还是忍不住要放慢脚步,期望见到她。
那天,我又在小木楼后边的芙蓉树下徘徊,被巫女保姆发现了。
“你又来了?”她的脸被夕阳映照得像一只熟烂了的黄金瓜。
“不是我打的弹弓,我没有那么大的弹丸。”我说。
“你说什么?是小白从车子上摔下来那天吗?可是,你逃跑了。既然不是你打的,那你为什么逃跑?”保姆气势汹汹地盯着我,“再说,我也没有向你问起这件事,你就主动来解释,明明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我想跟她把这件事说清楚,可鬼知道为什么,我的嘴直发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突然我像小偷似的撒腿逃去了。
“阿培,你这坏小子!”巫女愤愤地骂。
余宝知道这件事后,问:“你是不是偷过小白家的东西了?”
“没有”。
“那你干吗那么怕巫女?只有干了坏事才心虚呢。哎,你爱听小白弹钢琴,这是真的吧?”
“……”此时,我心里有一种被浓郁的花香裹住了的感觉。
“你是个复杂少年!”余宝模仿巫女的口气说。
密室钥匙转移到我手里,可我惹祸上身:家里莫名其妙被盗,高肯对我穷凶极恶。
密室的钥匙找到了,余宝变得轻松多了。他说即使暂时找不到密室也没关系,至少他占主动——没有钥匙,老熊就打不开密室。
可是,就在余宝踌躇满志的时候,事情发生了急剧变化。
一天午夜,继父突然推醒了睡着的余宝,问:“余宝,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偷了我的东西吗?”
余宝吓了一跳,但很快镇静下来:“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定要我点破吗?”
“那是你的事。”
“老老实实把钥匙交出来!”老熊怒目圆瞪。
“哗啦!”狡猾的余宝把家里的一串门钥匙扔到桌子上,说:“你打算把我扫地出门?其实用不着,我早就想离开这个家了。”
说着,余宝像一只黄鼬似的从被窝里钻出来,溜下床,开始穿衣服。
“余宝,你糊弄不了我!”继父连看也没有看桌子上的钥匙。“实话说了吧,余宝,你的小诡计只可以哄哄你的同学。”
继父的声音阴森得如同深夜的猫头鹰。他嘴里镶着的三颗大银牙,熠熠闪亮,仿佛含着一只蠕动着的毒蜥蜴。这让余宝不由地联想到电影里的黑社会老大,他想,说不定继父的秘密身份就是黑社会的。
想到这儿,他忽然感到了一种彻骨的恐惧,两条腿瑟瑟地颤抖着。平时他喜欢跟继父声嘶力竭地吵架,恨不能让薄荷巷子里的人都听到。而现在他蓦地失去了这种勇气,甚至想母亲和妹妹马上能从她们的房间走出来,把恐怖的继父拖走。
可是,母亲和妹妹的房间门一直没有开。她们没有被惊动。
余宝抓起书包就要开门,但被继父拦住了。
“把钥匙交出来!”
“已经交了。”
“那不是我要的!”
“别的钥匙我没有。”
“啪!”继父狠狠扇了余宝一记耳光。
耳光太响了,夜深人静就像雷劈的声音。这回,余宝的母亲被惊醒了,她跑出来,死死抱住怒不可遏的丈夫。余宝趁此机会冲出了家门。
后半夜余宝是在我家屋檐底下度过的。他就像一条愤怒的丧家犬,满腔仇恨地蜷曲在窗前,天还没完全亮,他就迫不及待地敲开了我家的门。
“阿培,帮我藏好它。”他把那串挖耳勺交给我,再三叮咛道,藏在一个好地方,不能让任何人看见。
我发现余宝的半面脸乌红乌红的,像乌鸡的脸。他让继父那一巴掌打得可不轻啊!就说:“以后,你搬到我们家住。”
“不行,这会引起老熊对你的注意。以后我们俩得分开,最好让老熊以为我们俩已经闹掰了。”他还说,暂时中止寻找密室的行动,躲过这阵风声再说。
我答应了。
我把密室的钥匙藏在了内裤里,不管白天还是夜里都让钥匙贴着我的身体。但是很快我就发现自己惹祸上身了。
那天,也就是余宝把钥匙转移到我手里的第二天,我们家莫名其妙地失窃了。
盗贼是从哪儿钻进屋里的,根本看不出。屋里的东西被翻得乱七八糟,就连我爷爷收藏的几枚动物标本腹中的干草都被掏空了,山雉标本的羽毛似乎也被仔细翻弄搜查过。但奇怪的是家里连一根针都没有少。
爷爷笑道:“这是一个真正的大盗贼哇,我猜他一定是走错了门。”
网友评论 欢迎发表评论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