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那边的风景(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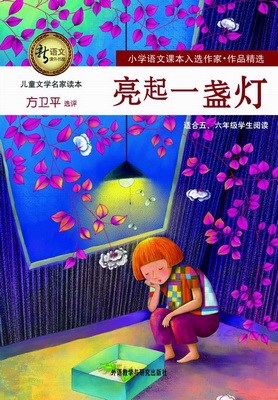
高洪波
从小生在大平原,没见过山。没见过山的孩子性情温和平静,就这样温和平静自然也平庸无奇地长到十三岁。除了在画报上和电影中看一看大山的平面图外,觉得自己离山太遥远,山是迷蒙的未来、陡峭的憧憬,偶或有梦,梦中登一种叫做高山的物体,登到山顶很累,就想飞翔——便向空中纵身一跃,身子骨一激灵,吓醒了。
大人们都是过来人,知道我梦中跳崖飞山,说这孩子拔节长个儿呐!
事实也是如此。没见过山,却不断梦山,梦见的山美丽、蒙眬、高耸入云,有大伞状的青松,还有大朵的蘑菇状的云朵,踩在脚下的石头不硬,像海绵。跳山崖时身轻如燕,从这块山头跃到那座山峰,只一步。
最后的结果当然免不了一脚踩空,继而是一激灵地醒来。定定神,知道自己平安无事地躺在东北大炕上,更知道在梦中又长高了一节,美滋滋的,觉得生活真有趣。
十三岁上告别科尔沁草原,一路奔南,奔向遥远的贵州。父亲工作调动,我们全家紧随,出发前知道一句民谣,是一位有学问的朋友念给我的,他是喜欢地理课的高中生,我心目中的偶像。他慢腾腾地吟道:“‘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知道吗?这就是贵州。”
从表面上看,他是怜悯、同情我的远行,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面临各种不可预测的困难,但我清楚地感受到这位老兄的嫉妒,一种困于小城无可奈何的嫉妒。兴冲冲地,我凭粗浅的知识反驳他道:“不可能,人怎么无三分银?再说谁还用银子,全用人民币,你说的全是老皇历。”看到我的不以为然,高中生摇摇头,悲天悯人地与我道别了。
很快地,我们登上旅程,过山海关,经北京,穿中原,越武汉长江大桥。山越走越多,有一阵全是钻隧道,一进隧道,就需紧急关上窗户,否则黑烟蹿入车厢,呛得你鼻涕眼泪直流。大山的厉害,终于开始领教。火车开到贵阳,一座典型的山城,我们小驻。父亲领我们游览黔(qián)灵公园,其实这公园就是一座黔灵山,沿山路台阶攀登,看满眼的修竹绿树,觉得山美极了,它仿佛是为了迎合人们的兴趣才生得那么秀,长得那么高。登到山顶,有一种平原上决计感受不到的快乐与豁朗,你冲白云喊一声,白云间有声音应和你;你拾一枚山石掷向山谷,有惊飞的小鸟啾啾地埋怨你;你采一把松针,有松香黏黏地留恋你的指甲,闻一闻,仿佛能闻到山本身的气息,一种平原所不具备的、清新又有几分粗犷的野味,用当前时髦的用语:混合香型。黔灵山就这样给我上了第一课。
山意味着沉重,水意味着轻灵;山代表着险峻,水代表着深沉。山举着高树,盘着如绳的小径,是大地的骨骼,故而山倔强;水托起小船,水花轻轻地吟唱,水是大地的血液,因此水温柔。
从我认识和理解了山的那一天起,我知道了“山有多高、水有多深”的山水共存道理,这是不可思议的一种自然景观。
曾有十年的时光,我走遍了云南的山山水水,在苦聪山、哀牢山的高山哨所,我用竹筒引来的山泉洗濯(zhuó)身心,那山林黝黑,可水色清澈;在景颇山、基诺山,我走访退伍的战友和插队知青,在大山的背影里我们饮山泉,无例外地,愈高的山那泉便愈美,沁出一丝甜味。或许,这泉水是优质的矿泉水,只是养在深山无人识罢了。有缘饮用,是何等快乐的一件事,尤其用那泉水冲凉的滋味,妙不可言。
我却一直没有机会登上军营对面那一座神秘的高山。从步入军营那一日起,这高山就遮断了我望乡的视线,它巍峨、傲慢,每天傍晚将橘红色的晚霞披在肩头,像一个土司山大王,阴天时雾气迷茫,偶或露出一点点鱼脊状的山尖;晴天里它一览无余,好像离我很近,一步便可跨上。这山很高,山半腰隐约有些房舍,山脚下有一条逶迤的铁路,铁路通向何方?房舍住的何人?一切都不可知。
这山横在我面前,渐渐地我意识到我是一个囚徒,而它是囚禁我的高墙。这想法激怒了我,我想走到山顶,让它在我的脚下狼狈,哪怕一刻钟,也值。同时我更迫切地想知道山那边的风景,就像一个好奇的邻居想知道一下别人的秘密——山那边肯定有秘密!
择一个训练的日子,背上我的电台,同伙伴直奔那军营对面的山。出发前我充满兴奋与快感,伙伴是一个老兵,从容地备好面条、炊具,又包上一包食盐、一块瘦肉,我们计划中午到达山顶,用电台同山下联络,然后野炊完毕下山。
事实上山路很好走,我们先穿过一条小河,由山脚处的村寨登山。不一会儿人烟渐稀,小路却很平,不像想象中那么陡峭。缓缓地沿小路绕上山,两小时后到达神秘的房舍,这其实是一座破败的古庙,内中住着茶场的职工。小憩后继续登山,直到这时山路才有几分陡峭。
在一块大石旁坐定,向山下望去,我的军营整整齐齐地卧在小小的坝子上,一排排土黄色的营房,掩映在高大的桉树下,极像小时候搭过的积木。
望一眼山顶,已不太遥远。刚准备起身,迎面走过一队农民,原来白云深处还有他们的土地,几个年轻的姑娘嘻嘻哈哈打趣着我们,问我们到山顶去干什么。我说这可是军事秘密,她们一撇嘴,摇摇头走了。临走时一个姑娘扔下一句话:“那山顶上除了风,啥子也没有!”
我们终于到达了山顶。山顶很平坦,左右望去,果然一无所有。我努力想看清楚山那边的风景,除了树就是树,再就是远方隐隐约约的一座湖泊,看得不太分明,绿蓝相间的颜色很轻易地被蓝天融化,说它是湖,仅只是我的臆(yì)测。
我们支起电台,调好频率,与连队联系,无线班长的声音清晰地响起,这是一个乐天派河南老兵,他建议我们煮面条时顺便打只兔子。大家在电台里调侃几句后,关机,煮面。
应该说这顿面条奇香无比。尽管没猎到什么野兔,可是爬山的饥饿是最好的调味品,脸盆里的面条被我们用树枝筷子捞得一干二净,连汤都没剩一口。
怎么说呢,山那边的风景远不如山顶上的野炊有味道,下山时我有几分懊丧地思忖(cǔn)到。
回到军营已近黄昏,疲惫不堪的我放下背上的无线电台,再扫望一眼屏障式的大山,发现虽然晚霞一如既往地被它披在肩头,可我却再也没有了从前的心态。我觉得它一点也不傲慢,相反是一种理所当然的风度。山嘛,就该有山的样子!
或许,我不去窥视山那边的风景更好吧?谁知道呐。熄灯号尚未吹尽,我已沉沉睡去,毕竟爬了一天山,太累了。
那一夜,从那一夜起,我再也没有梦见过登山。
阅读高洪波
成长的身影
方卫平
高洪波为孩子们写诗的时候,常常忘掉了自己。他走进一个孩子的思想和心灵中,用诗行来表现这个孩子对童年生活的感受和思索。这些感觉和想法有的散发着自然的诗意,有的饱含着生活的温暖,有的纯然是一些调皮的点子,还有的则藏着孩子心里小小的苦恼。这样,从他的诗歌里就走出来了许多个姿态各异的童年身影。这些身影叠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生动而又多彩的现代童年的形象。
网友评论 欢迎发表评论
|
|
|
|




